莫言:秋天对于我只是一大堆凌乱的印象
这几日走在下班路上,觉得腿上凉了,好像该加双丝袜,白天抬头看云彩,发现它们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远。没错,是秋天来了。于是我翻了翻书,看看作家们在秋天都写了些什么。
在莫言的眼里,秋天的北京只是一大堆凌乱的印象,看书、喝茶、抽烟,秋天是隐在生活背后的;三毛觉得,秋天是异国他乡寂寞的催化剂,在相互依存中平添悲凉的底色;张晓风认为秋天代表了生命的深度,她说,我爱秋天,以我全部的敬畏与虔诚。

电影《秋天的故事》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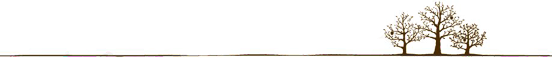
莫言:《北京秋天的下午》
据说北京的秋天最像秋天,但秋天的北京对于我却只是一大堆凌乱的印象。因为我很少出门,出门也多半是在居家周围的邮局、集市活动,或寄书,或买菜,目的明确,直奔目标而去,完成了或得手了就匆匆还家,沿途躲避着凶猛的车辆和各样的行人,几乎从来没有仰起头来,像满怀哲思的屈原或悠闲自在的陶潜一样望一望头上的天。
据说秋季的北京的天是最蓝的,蓝得好似澄澈的海,如果天上有几朵白云,白云就像海上的白帆。如果再有一群白鸽在天上盘旋,鸽哨声声,欢快中蕴涵着几丝悲凉,天也就更像传说中的北京秋天的天了。但我在北京生活这些年里,几乎没有感受到上个世纪里那些文人笔下的北京的秋天里美好的天。那样的秋天是依附着低矮的房舍和开阔的眼界而存在的,那样的秋天是与蚂蚁般的车辆和高入云霄的摩天大厦为敌的,那样的天亲近寂寞和悠闲,那样的天被畸形的繁华和病态的喧嚣扼杀了。没有了那样的天,北京的秋天就仅仅是一个表现在日历牌上的季节,使生活在用空调制造出来的暧昧温度里、很少出门的人忘记了它。
我的午休时间很长,十二点上床,起床最早也要三点,有时甚至到了四点。等我迷迷瞪瞪地起来,用凉水洗了脸,下午的阳光已经把窗上的玻璃照耀得一片金黄了。起床之后,我首先是要泡上一杯浓茶,然后坐在书桌前。如果老婆不在眼前,就赶紧地点上一支烟,喝着浓茶抽着香烟,那感觉十分美妙,不可以对外人言也。
喝着茶抽着烟我开始翻书,乱翻书,因为我下午不写作。我从来也没养成认真读书的习惯,拿起一本书,有时候竟然从后边往前看,感到有趣,再从头往后看。从过了四十岁后,我再也没有耐心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了,无论是多么精彩的书。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知道,但要改正也难了。看一会儿书,我就站起来,心中感到有些烦,也可以叫无聊,就在屋里转圈,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懦弱的野兽。有时就打开了那台使用了十几年的日立牌电视机,21英寸的,当时是最好的,是用了我第一次出国的指标在出国人员免税店买的。日本货的质量,虽然近年来也频频出问题,但我家这台电视机的质量实在是好得有点惹人烦。十几年了,天天用,画面依然清晰,声音依然立体,使你没有理由把它扔了。电视里如果有戏曲节目,我就会兴奋得浑身哆嗦。和着戏曲音乐的节拍浑身哆嗦,是我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我一手捻着一个羽毛球拍子使它们快速地旋转着身体也在屋子里旋转,和着音乐的节奏,心无杂念,忘乎所以,美妙的感受不可以对外人言也。

秋日的香山红叶
按说北京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秋天有三个月。中秋应该是北京最好的季节,其实,中秋无论在哪里,都是最美好的季节。苏东坡的千古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是在我的故乡做知州时写的,可见那时的月亮是何等的明亮。那时还没有吃月饼的习俗,如果有,苏东坡不会不写的。月饼之所以有馅,是因为当时在月饼里夹上了造反的信号,要造蒙古人的反。我少时听一个去内蒙古贩卖过牲口的人说,八月十五夜里,蒙古人要到草里去藏一夜。我总是感到那中秋节是北京人发明的一个节日,因为北京曾是元朝的大都。元大都的城墙遗迹,就在我曾经住过的小西天附近,那上边有很多树,如果在秋天的下午,站在元大都城墙上的树林子里,也许会更多地感受到一些北京秋天的美丽吧。也许我应该去一次,为了这篇文章。
现在是北京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打破下午不写作的习惯,坐在书桌前,回忆着古人关于秋天的诗句来结束这篇文章:“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秋风忽洒西园泪,满目山阳笛里人”,“枫叶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古人有“悲秋”之说,大概是因为秋天的景象里昭示着繁华将逝,秋天的气候又暗示着寒冷将至,所以诗中的秋天总是有那么几分无可奈何的凄凉感,但也有唱反调的。李白就说:“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刘禹锡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杜甫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黄巢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放百花杀”;毛泽东说:“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但即便是反调文章,也没有把悲变为喜,只不过是把悲凉化为悲壮而已。
三毛:《秋恋》
她坐在拉丁区的一家小咖啡室里望着窗外出神,风吹扫着人行道上的落叶,秋天来了。
来法国快两年了,这是她的第二个秋,她奇怪为什么今天那些风,那些落叶会叫人看了忍不住落泪,会叫人忍不住想家,想母亲,想两年前松山机场的分离,想父亲那语不成声的叮咛……她仿佛又听见自己在低低的说:“爸、妈,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就像千百次她早晨上学离家时说的一样,走了,走了……哦!妈妈……她靠在椅背上,眼泪不听话的滴下来。她打开皮包找手帕,她不喜欢自己常常哭,因为她害怕自己一哭就要哭个不停了。她低下头燃了一支烟,她有些埋怨自己起来。她记得半年前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她记得她曾说:“妈妈,我抽烟了,妈妈,先不要怪我。我不是坏女孩子,我只是……有时我觉得寂寞难受……不要再劝我回去,没有用的,虽然在这儿精神上苦闷,但我喜爱飘泊……”她奇怪在国内时她最讨厌看女人抽烟。她狠狠地吸了一口。

《爱在黎明破晓前》剧照
咖啡凉了,她预备回去,回她那间用廿元美金租来的小阁楼兼画室。
抬头望了望窗外,黄昏了。忽然,她发觉在窗外有一个陌生的中国青年向她注视着,并且似乎站了很久了。她迷乱地站在那儿,不知怎么开口招呼他。他从外面推门进来了。“坐吧!”她指着对面的椅子低哑地说着。他们没有交谈,只沉默地互相注视着,她觉得有些窘,下意识的拿出了一支烟,自己点了火。
“抽烟?”他摇了摇头。
小店的胖老板亲自端来了一杯咖啡,朝她扮了个鬼脸,大概是替她高兴吧!这个每天来喝咖啡的苍白寂寞的中国女孩子找到朋友了。她觉得有些滑稽,只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就使我那么快乐了吗?她再看了他一眼,他像是个够深刻的男孩。
“我在窗外看了你很久,你心烦?”他终于开口了。“没什么,只不过是有些想家。”她狠狠的吸了一口烟,逃避的把眼神散落到窗外,她害怕人家看透她。
“你从台湾来?”他问。
“台湾,”她缓缓的,清清楚楚的回答他。
“你住过台北没有?你知道,我家在那儿。”她掠了掠头发,不知应该再说什么。他没有回答她,却注视着她掠头发的动作。
“你来巴黎多久?”
“两年不到。”
“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画画。”
“生活还好?”
“我来时带了些钱,并且,偶尔我可以卖掉一张小画……”他沉默了好久,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当我在窗外看到你,第一眼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她装着没听见他的问话,俯下身去拨动烟灰缸。“刚才我问你曾在台北住过?”
“是,我一直住在那儿,我是海员,明年春天我跟船回去。”他的声音低哑起来:“我们的职业就是那么飘泊,今天在这儿,明天又不知飘到里哪里了……” “招商局的船极少极少开到这儿。”她说。
“不是招商局的,我们挂巴拿马的旗子。”
“什么时候开船?”
“昨天来的,后天清早开中东。”
后天,后天。她喃喃的念着,一下子觉得她对现在的一切留恋起来。她忽然想冲动的对他说,留下来吧!即使不为我,也为了巴黎………多留几天吧!然而,她什么都没有说,他们不过是两个天涯游子偶尔相遇而已。她把两杯咖啡的钱留在桌上,站起身来,像背书似的对他说:“很高兴今天能遇见你,天晚了,就要回去……”一口气说完了,她像逃似的跑了出去。她真恨自己,她知道她在这儿寂寞,她需要朋友,她需要快乐。她不能老是这样流泪想家……他像是一个好男孩子。她恨自己,为什么逃避呢,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踉跄的跑上楼梯,到了房里,她伏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她觉得她真是寂寞,真是非常非常寂寞……
第二天早晨,她披了一件风衣在巴黎清冷的街心上独步着,她走到那家咖啡室的门口,老板正把店门拉开不久,她下意识的推门进去。
中午十一时,她仍坐在那儿,咖啡早凉了,烟灰散落了一桌。昨天,他不过是路过,不会再来了……忽然,她从玻璃反光上看到咖啡室的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进来,他穿了一件翻起衣领的风衣。他走过来,站在她身后,把手按在她的肩上。她没有回头。只轻轻的颤抖一下,用低哑的声音说:“坐吧!”就像昨天开始时一样,他们互相凝视着说不出话来。他伸过手臂轻轻拿走了她的烟。
“不要再抽了,我要你真真实实的活着。”
他们互相依偎着,默默的离开那儿。

电影《当哈利遇到莎莉》剧照
夜深了,她知道时候到了,她必须回去;而他,明早又四处飘泊去了。她把花轻轻的丢在河里,流水很快的带走了它。
张晓风《秋天·秋天》
满山的牵牛藤起伏,紫色的小浪花一直冲击到我的窗前才猛然收势。
阳光是耀眼的白,像鍚,像许多发光的金属。是那个聪明的古人想起来以木象春而以金象秋的?我们喜欢木的青绿,但我们怎能不钦仰金属的灿白。
在我们的城市里,夏季上演得太长,秋色就不免出场得晚些。但秋是永远不会被混淆的——这坚硬明朗的金属季。让我们从微凉的松风中去认取,让我们从新刈的草香中去认取。
已经是生命中第二十五个秋天了,却依然这样容易激动。正如一个诗人说的:
“依然迷信着美。”
是的,到第五十个秋天来的时候,对于美,我怕是还要这样执迷的。
那时候,在南京,刚刚开始记得一些零碎的事,画面里常常出现一片美丽的郊野,我悄悄地从大人身边走开,独自坐在草地上。梧桐叶子开始簌簌地落着,簌簌地落着,把许多神秘的美感一起落进我的心里来了。我忽然迷乱起来,小小的心灵简直不能承受这种兴奋。我就那样迷乱地捡起一片落叶。叶子是黄褐色的,弯曲的,像一只载着梦的小船,而且在船舷上又长着两粒美丽的梧桐子。每起一阵风我就在落叶的雨中穿梭,拾起一地的梧桐子。必有一两颗我所末拾起的梧桐子在那草地上发了芽吧?二十年了,我似乎又能听到遥远的西风,以及风里簌簌的落叶。我仍然能看见那载着梦的船,航行在草原里,航行在一粒种子的希望里。

南京的秋天
又记得小阳台上的黄昏,视线的尽处是一列古老的城墙。在暮色和秋色的双重苍凉里,往往不知什么人又加上!阵笛音的苍凉。我喜欢这种凄清时美,莫明所以地喜欢。小舅舅曾经带我一直走到城墙的旁边,那些斑驳的石头,蔓生的乱草,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长大了读辛稼轩的词,对于那种沉郁悲凉的意境总觉得那样熟悉,其实我何尝熟悉什么词呢?我所熟悉的只是古老南京城的秋色罢了。
后来,到了柳州,一城都是山,都是树。走在街上,两旁总夹着橘柚的芬芳,学校前面就是一座山,我总觉得那是就地理课本上的十万大山。秋天的时候,山容澄清而微黄,蓝天显得更高了。
“媛媛,”我怀着十分的敬畏问我的同伴,“你说,教我们美术的龚老师能不能画下这个山?”
“能,他能。”
“能吗?我是说这座山全部。”
“当然能,当然,”她热切地喊着,“可惜他最近打篮球把手摔坏了,要不然,全柳州、全世界他都能画呢?”
沉默了好一会。
“是真的吗?”
“真的,当然真的。”
我望着她,然后又望着那座山,那神圣的、美丽的、深沉的秋山。“不,不可能。”我忽然肯定地说,“他不会画,一定不会。”
没有人会画那样的山,没有人能。
而日子被西风刮尽了,那一串金属性的、有着欢乐叮声的日子。终于,人长大了,会念秋声赋了,也会骑在自行车上,想像着陆放翁“饱将两耳听秋风”的情怀了。
秋季旅行,相片册里照例有发光的记忆,还记得那次倦游回来,坐在游览车上。
“你最喜欢那一季呢?”我问芷。
“秋天,”她简单地回答,眼睛里凝聚了所有美丽的秋光。
我忽然欢欣起来。
“我也是,啊,我们都是。”
她说了许多秋天的故事给我听,那些山野和乡村里的故事。她又向我形容那个她常在它旁边睡觉的小池塘,以及林间说不完的果实。
车子一路走着,同学沿站下车,车厢里越来越空虚了。
“芷,”我忽然垂下头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同伴一个个下车了,座位慢慢地稀松了,你会怎样呢?”
“我会很难过。”她黯然地说。
我们在做什么呢?芷,我们只不过说了些小女孩的傻话罢了,那种深沉的、无可如何的摇落之悲,又岂是我们所能了解的。
但,不管怎样,我们一起躲在小树丛中念书,一起说梦话的那段日子是美的。
而现在,你在中部的深山里工作,像传教士一样地工作着,从心里爱那些朴实的山地灵魂。今年初秋我们又见了一次面,兴致仍然那样好,坐在小渡船里,早晨的淡水河还没有揭开薄薄的蓝雾,橹声琅然,你又继续你的山林故事了。
我并非不醉心春天的温柔,我并非不向往夏天的炽热,只是生命应该严肃、应该成熟、应该神圣,就像秋天所给我们的一举样——然而,谁懂呢?谁知道呢?谁去欣赏深度呢?
远山在退,遥遥地盘结着平静的黛蓝。而近处的木本珠兰仍香着,(香气真是一种权力,可以统辖很大片的土地),溪水从小夹缝里奔窜出来,在原野里写着没有人了解的行书,它是一首小令,曲折而明快,用以描绘纯净的秋光的。
而我的扉页空着,我没有小令,只是我爱秋天,以我全部的虔诚与敬畏。
- 上一篇: “新老人”:60 后养老之变
- 下一篇: 村上春树:面对深不见底的孤独,毫不畏惧地拥抱它





